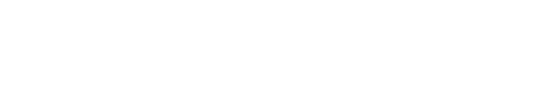一、思想基础
梁启超他的祖父、父亲,都没有很高的功名,尤其是他的父亲,但都很注意让他读书,所以他十四岁年纪轻轻就考中了秀才。然后就送他进了广州的学海堂,这是一个很有名的书院,到十七岁他就中了举人,举人就是省一级的这个科举考试已经通过了。他应该是从小就是有天才的,读书人的根苗就已经显示出来,然后到了十八岁,就拜见了康有为,受康有为的影响,他就开始追随康有为,在这之后就到了万木草堂,跟随康有为学习。他后来讲,“先生教之以陆王心学”,就是康有为教给他哲学思想,你不仅仅要知道字怎么解释,一个书你不仅看懂它,还要知道它的义理大义。除了哲学思想以外,还有史学,另外康有为还为他们讲西学之大概,所以万木草堂这个教育在近代还算新的,康有为把西学的大概跟他讲,所以梁启超在二十岁以前,他这个基础,包括传统的小学的基础,传统的哲学的基础,然后史学和西学的一些基本东西,他都掌握了。他的学问底子非常好。他的大思想的底子从哪来呢?那还是康有为门下,在万木草堂学到的那些东西。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他就流亡日本,但是他这段可以说开始他新一段的文化人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写了大量的文章著作,对于国人的启蒙和冲破旧传统的那种震撼,他起了最大的一个作用。
比方说他当时在日本,他写的《少年中国说》,少年富则中国富,少年强则中国强,那可以说对当时的国内青少年,应该说震动很大。还有《新民说》等。
这些东西,应该说1890年代出生的人没有不受他的影响,比如说毛泽东,比如说胡适,都是受到他的这些在日本初期写的这些重要文章的影响,那是影响了一代人。他基本观点就是说,中国传统的文化很重视私德的培养,我们今天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要注重培养我们人民的那种公德,其中当然最重要的就是爱国心。另外他还那时候写了一个著作叫《新史学》,我们整个近代以来中国的史学发展,其实就是一个“新史学”的发展,这个新史学的奠基就是在梁任公。它的新在什么地方呢?他说我们以前讲那个史学,是以帝王为中心的,都是讲皇帝怎么样,围着皇帝转的,他说史学应该发展、应该进步、应该打破,新的史学就是要以民族和文化为中心,而不是以皇帝为中心,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对史学观念的改变,所以应该说,他开创了整个二十世纪中国的新史学的发展。
梁先生他一生的好多思想都有变化,这个是大家都知道的,他自己也说他自己是经常变,但是我觉得这个变不是没有立场的善变,这个变表示他对思想、思考的一种深化。比如说他对中国的不好的地方有认识,对西方的优点也有认识,然后他提倡启蒙;然后过一段,他又对西方的缺点也有所认识。以前是把中国的缺点跟西方的优点相对,但是他自己思想不断变化,对西方的缺点也有新的认识,比方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带来了对西方文化的反思,所以使他对这个很多问题有重新的思考。所以我觉得变不是坏事,不能一个人就是一直不变,一直不发展,这个变其实代表着一种深化、反思,这是一个问题。再有比如科学的问题,梁先生始终是很赞成引进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文明,但是作为一个哲学家他并不认为这个科学技术是最重要的,还是一个健康的人生观、一个人生的哲学是最重要的。他认为两者并不矛盾,他希望把近代西方的这种科学技术文明,跟中国传统的这种积极的人生观结合起来,中西形成一种融合,这是他的思想特点。
二、清华学校
梁启超非常注重德育,我们今天讲他的国学的成就,不讲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其实他是非常重视德育的一个人。1905年他还在日本的时候,1903年他从美国回来,他认识就有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促使他写了一本书,叫《德育鉴》,这《德育鉴》就是把他在康有为门下学习的时候,他摘记的那些古代的那些个人修养的语录编成册,他就是来使大家在新的时代仍然能够从这些古代的修养文化里面,培养自己的人格。这些摘录本来是给自己看的,是鼓励自己的,1905年他编出了《德育鉴》,就是让大家都作为一个镜子来照。然后他回国到清华,1912年他回国,1914年冬天他到清华,他就借住工字厅写书,同时他就在同方部讲演,给清华学生讲什么呢,清华当时是留美预备学校,学生都是准备留美,那就讲怎么样培养自己的“君子”人格,他的主张就是《周易》里边有两句话,就是“自强不息”和“厚德载物”。就是现在清华的校训。
因为《周易》里面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还有一句就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他就说第一句话讲的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不懈地向上,就是人要不懈地向上追求。然后下一句讲我们要有一个宽阔的胸怀和度量。说清华的学生就应该照着这个做君子的人格,来改变我们这个社会,来发展我们的文明。所以他讲给学生的,都是一些德育方面、人生的教导。当时他还讲了,清华的学生是要留美,但是你不要忘了国学是立国之本。可是国学怎么讲、怎么掌握呢?他就用这两句话,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所以这两句话就成了清华的校训。
梁启超先生,他当年在教国学方面,他是如何来教育的呢?他非常注意知识跟道德的平衡,他的讲演讲课都不离开这点,你比如说,1917年他在清华有个讲演,他专门讲《学生自修之三大要义》,自修不是我们今天讲的知识的自修,其实是全面修养的自修,三大要义就是做人、做事、做学问。做人的要义就是要反省克己,做事的要义就是精力要集中,学问之道的要义就是学以致用。所以你看,学以致用,精力集中是都在下面,最前面的是反省克己,就是要增进自己的德性。所以他对国学的把握、理解,他教学、教书,始终不少这一条,就是德性的教育。他强调,国学的常识是两样,中国历史之大概,中国人的人生观。就是说学习国学一方面要掌握中国的历史文化,一方面要学习中国文化的人生观。
大概1923年,他就有一次回答学生的问题,就讲国学是有两条大路,因为从1919年开始,有所谓整理国故的运动,这是胡适推动的,梁启超就说治国学有两条大路,一条是文献的路,文献的路就是整理国故,他说可是你光是整理国故,用这样的一种方法来对待国学,他认为这个是不完整。所以他说还有一条路叫德性的路,就是德性的学问,国学不仅仅是一个文献的学问,国学还是一个德性的学问。刚才讲他1910年代他已经经常到清华讲演,因为他也喜欢清华,当然他也把孩子梁思成等送到清华念书,所以他对清华也多一份眷顾吧,然后他1920年的时候,他就到清华一个冬天,讲《国学小史》,讲五十多次。
当时他还没有名义,到1922年,他就有正式名义,他就接受了正式聘他为清华学校的讲师,讲师不是说你那个学问地位,如果你不是全职在这儿工作,就是讲师,他那个时候开的课就是《中国学术史》。
他的讲课,有一个最好的记载,就是梁实秋先生,他记述的1922年梁先生一个讲演。说梁先生这个人,他是短小精干,他那个身材可能不是很高,但是说他是风神潇洒,然后说是左顾右盼,这是讲他那眼睛,光芒四射,就是他眼睛是非常有光芒的,然后呢,当时他是略有一些秃顶,他是讲广州官话,我看有些记载说梁先生话很不容易听,不容易听得懂,所以有人只能听五六成,但是你看梁实秋的文章,说他虽然是讲的广州官话,但是每一个字,他发音很清晰,所以你每一个字还是听得懂的。而且他甚至认为,他说如果梁任公不讲广州官话,讲成这个北京的普通话,就没味道了。
梁先生讲课很兴奋,他那个头也比较大,然后冒汗,他上课的时候,有的时候他的儿子梁思成先生,就在台下坐着听。然后因为他经常写板书,经常就说“思成,擦擦”,就是让梁思成擦黑板,去帮他擦那个黑板。
他把古文文献都记在脑子里,记很多东西,据说他当时到清华讲课的时候,他已经快五十岁了,他就是靠背。但是有的文献也不是说马上都能够背出来,有的时候他背不出来呢,他就敲那个脑袋,他一敲脑袋呢,学生也紧张,为什么呢,他一敲脑袋时候这不就停了嘛,就在那儿想,学生就跟着着急,等到想起来了,他就背出来了,学生也很高兴,所以他是老爱敲脑袋的。
梁先生这个人,他的形象就是天真烂漫、富于热情、目光如炬、亲切随意,具有人格的伟大感召力,这是他的学生们一致公认的。
三、清华国学院
到了1925年才正式变成清华国学院的导师、教授。梁启超是清华国学院的核心,但为什么在四大导师之中,梁启超排名在第二位?这恐怕跟梁先生的这个人品、性格有关系,要按照当时的影响来说,最大的是梁先生,但梁先生是一个非常谦让的人,在当时的国学院里面,他事事都推王先生在前面,所以人家说,整个国学院的核心人物是梁先生,但他事事都自处于观堂先生之下。这是他的高风亮节。
梁启超特别注重德行的教育,他对于如何做人是怎么论述的呢?在清华国学院刚开始,就是一开学,他就特别注意。国学院一开学,他就有一个讲演,讲清华国学院必须要办两件事,就是要办好这清华国学院,一个要养成学生的做学问的能力,一个是要养成他做学问的好习惯。第一个养成做学问的能力,他提了四点,就是“明敏、密察、别裁、通方”。明敏就是你要有很敏锐的眼光,密察就是你观察的时候心思要很细腻。然后别裁,是你能鉴别,鉴别真伪、有无、主次,特别主次很重要,鉴别主次。通方就是你对这个事物的研究,要彻头彻尾,彻里彻表,要这样。他讲,国学院要培养人,第一条,就是要养成学生做学问的能力,而能力他是从这几个方面来讲的。第二个是养出做学问的好习惯。就是“忠实、深切、敬慎、不倦”。敬慎就是你要非常谨慎,不倦就是不能懈怠,做学问一定要忠实,忠实就是不能作假,我觉得这些要求,包括做学问的这些习惯,做学问的这些能力,都是具有超越时代的意义,我们今天也要注意培养的。
后来他晚年到1927年,有一次著名的北海之行,就留下一段北海讲话,那北海讲话,最重要的还是讲这个,一方面是做学问,一方面是做人。所以他说,说我讲了那么多,归结就两条,第一条就是我们要培养一种人,这种人是什么呢,是不跟着这个潮流走的,他讲的潮流是那个时代不好的潮流,每个时代都有一些潮流,是大众跟着的,可是那个潮流不见得是很健康的,你要培养能够立定自己的脚跟,站稳自己的脚跟、理想的人,要培养这种人。另外,你要培养一种新的国学研究的人才,这个人才不是不关注潮流,而要注意新的学术潮流。所以做人,不能都跟着那个社会潮流走,可是做学问,这个新的潮流你必须要注意。所以他是总是两方面都要讲到。
谢国桢先生,他是清华国学院的学生,梁先生对学生非常照顾,他为什么请这个他的学生谢国桢来教他的家里的子弟,其实就是给他一份收入,然后谢国桢先生在这个过程中也得益很多,为什么,因为他等于住在这个梁先生家里,梁先生这个有时候写书的这些过程,他会亲身看到,而且梁先生在写累了的时候就把他们叫进来,把谢国桢先生就叫进来,然后就讲他过去的历史。他有一次,在讲那个戊戌变法的历史的时候,他就顺嘴就背出这个汉代董仲舒的《天人三策》,结果谢先生就很惊讶,说您连这个董仲舒《天人三策》都能背出来,他说我不会背董仲舒的《天人三策》我怎么能够上万言书呢!所以这些都是对学生的关照,是一种对他们的一种教育,身教。还有周传儒,因为梁启超每周一二三四五他都住在清华,住在清华呢,他是礼拜三讲课,讲“儒家哲学”,周传儒记录。周传儒先生写过关于清华国学院和梁任公的很多的回忆的文章,他也是受惠梁先生的照顾不少,因为他那时有点穷,梁先生就安排他在松坡图书馆,做目录,抄卡片,给二三十块钱一个月,其实不算太少。但是他还有弟弟上学,负担挺重,梁先生就说再给他升个官,在这些编目的人里边,他当小头目,叫提撰,又增加二三十块钱,拿五六十块钱,他说我上学的时候,从梁先生手上拿了1000多块钱,当时那个钱是很值钱的,所以可见梁先生给他照顾是很多的。所以他晚年写文章是很有感情的。梁先生还介绍刘节到北京图书馆。
梁任公他是他的学术是非常博通的,他也是多才多艺的,但是另一方面他有的时候,也有不得已的地方,你比如说,松坡图书馆,用蔡锷的名字命名的,这是他创立的,那么政府就拨了这块地,就是北海这个地给他,但是没钱,没钱怎么办?他就要靠卖字来筹款,所以他从清华每次回到北海住的时候,每天吃完饭,抽一支烟,七点钟就开始写字,一个字八块钱,八块大洋,谢国桢也好,周传儒他们也好,学生他们就管拉纸,他就写字。然后用这些钱来筹款。当然了,他们那两位拉纸的先生呢,有时候也可以塞点私活,就是有人要求字,就求他们学生。梁先生写字时,只管问下一个是谁,他们就说下一个是给谁,他就写在那儿。写字就是筹款,来筹建这个图书馆,其实他还兼了北京图书馆的馆长。
四、大师地位
在历史上,梁启超先生和胡适先生,就关于国学的入门的书目曾经有过争论,当时大概在1923年吧,大概1923年初的时候,清华的学生就给他们写信,应该是给胡适和梁启超同时发的信,清华学生写信说,我们要出国,,我们还要掌握一些国学,怎么掌握呢,能不能请先生给我们开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就是要他们开一个最低限度的书目,后来胡适就有文章,就叫《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但是他开了很多,大概有一两百种,他是两个系列,一个是思想史的系列,一个是文学史的系列。他不是开了这个嘛,然后学生就又给他写信,说胡先生,我们是要一个最低限度书目,你给我们开这么多,我们在清华这几年也念不完,我们带到美国也没法念。后来他就说,那我就在这上画圈,他就画了三十五个圈,但是这三十五个圈儿,应该说它那个条理不是很清楚。梁先生当时没在北京,他接到这个信,他就用记忆,他也没怎么查书,也写了一个书目,也写了一个,这个书目也不少,而且每本书他都说有什么版本,这个书大概意思是什么,大概也有一两百种。但是,他的好处是什么呢?他当时就在下面指出说,那个书目太多了,还有一个真正是最低限度的,二十五种。这二十五种他是很有条理的,就是按照我们四部的分类,第一部就是经部的四书五经,第二部史部,《战国策》《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资治通鉴》,然后子部,《老子》《庄子》《墨子》《荀子》《韩非子》,这是子部里最重要的,最后集部,楚辞、文选,李白的集子、杜甫的集子、白居易的集子,他就按经史子集分类里面找最重要的这二十五部书,非常清楚。所以他就有点讥笑胡适,说你这个国学书目里面,《史记》都没有,《资治通鉴》都没有,有那个《九命奇冤》,那是最低书目吗?他说不瞒你说我梁某人就没看过那个《九命奇冤》,你能说我连最低的国学知识都没有吗?
今天我们在回顾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日子,能够给今天做学问的人以什么样的启发呢?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主题,我觉得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这些年,因为国学热,讲了很多的国学,国学也确实包含了很多的方面,但是国学里面内在包含的这个德性的学问这方面应该说强调的不太够。特别是因为胡适,他在近代学术的影响比较大,他提出整理国故,造成国学就是一个整理国故的学问。因为在胡适的定义里头,国学是什么?国学就是整理国故的学问,而整理国故的学问对于胡适来讲,不涉及哲学的人生观的发扬继承,而是文献和历史的了解整理。所以我觉得梁先生在这方面,不愧是一个大思想家、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对整个国学的把握,对我们今天来讲,应该有指导意义。所以我们今天的清华国学院,我们重印了梁先生的《德育鉴》,因为这个《德育鉴》,很多二十世纪的文化名人都受这本书影响,我们编的,然后做了一些注解,做了一些简单的注解,让出版社来发行,就是想至少在清华的校园文化里面,我们把梁先生原来的工作,拿给大家,让学生不仅在今天用现代的那些口号,讲一些素质教育,看看我们的先贤,用什么的办法来修养自己,我们用这个方法来提高我们的素质。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做的一个事,我们觉得还蛮欣慰的一件事。
有人问梁启超是不是国学大师,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吧。1912年的时候,马相伯先生,就是复旦的创始人,很有名的教育家,他当时就建议,就创立“函夏考文苑”,仿照法兰西学术院,那当然就要有院士,提名一共有二十多位,首席是四位,其中就有梁启超,其余是严复、章太炎和马相伯。这是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就中国的国学来讲,整理国故的时代,二十年代,大家有一个共识,这共识就是说章太炎先生是南方学术的泰山,就说梁任公先生是北方学术的这个北斗,所以是一南一北,也是承认他们两个是当时国学的最高的代表。另外就是清华国学院成立前,在1924年,清华的曹云祥校长,跟胡适请教办国学院的办法的时候,他本来是想请胡适来主持,因为胡适是清华史前期的校友,他是头两批庚子赔款生,就是清华园还没建好的时候,没让他们在这念书,就直接放洋了。清华想请胡适筹建国学院,胡适说我不配,说你要请一流的学者,要请三位大师,他的排名就是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来讲,梁先生作为国学大师的这个地位,应该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是公认的了。他的学术成就也应该说是多方面的,具有博通的成就,而且开风气,有很强的示范作用,像在先秦诸子方面(《墨子学案》、《老子哲学》、《先秦政治思想史》),在清代学术方面(《清代学术概论》,《近三百年学术史》),在佛教史方面(《中国佛教史》),在新史学的研究方法方面(《中国历史研究法》),贡献都非常大。郑振铎说他是大思想家,动手便有极大的格局,有通盘的打算,上下古今大规模的研究,有力吞全牛的气魄,确实是这样。
梁启超曾给学生题联“万事祸为福所倚,百年力与命相持”,前一句表示乐观主义,祸事不可怕,祸的后面是福,这就是乐观。后一句表示奋斗精神,这是发扬墨子尚力的思想,敢于和命运斗争。他一生最推崇的是曾国藩的话“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作为自己的座右铭,充分体现了他的儒家人生观。所以徐世昌评价说他是“以德性言之,当推海内第一人”。徐志摩称他是“完美学者的形象”、“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人”。他的确是中国近代一位伟大的圣贤人物。
(本文是作者在央视文明之旅节目“梁启超在清华”的讲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