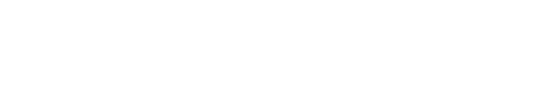世人都晓得,名师固然出高徒,高徒同样也能出名师。二十年前,具体说是2005年5月25日,我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演讲,讲稿以《大师的意义以及弟子的位置——解读作为神话的“清华国学院”》为题,初刊《现代中国》第六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2月),后收入我的《读书的风景——大学生活之春花秋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019年)。文章的基本立论是:“机构”“前辈”与“后学”,这三者的合力,共同成就一个个学术史上的“神话”。众所周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俗称清华国学院)成立于1925年,1929年便黯然落幕了。前有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1922)、东南大学国学院(1924),后有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1926)、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8),为何夹在这中间、仅存在四年的清华国学院最为熠熠生辉,吸引无数公众的目光?我猜想其重要缘故:这是一个头尾完整、充满悬念、略带幽怨、可以寄托各种情怀的学术传奇。当初异军突起,成绩斐然,可很快就像樱花一样在最灿烂的时刻凋谢,让后人充满遐想与感怀。
别看清华国学院存在时间短,但培养的学生并不少。四届学生中,前两届的表现尤其精彩;完成学业的74人,日后多有名扬四海的。究其原因,与办学经费充足有很大关系——聘专任教授、给学生发奖学金、办学术杂志、举行北海茶话会等,这些都是北大等所不具备的。除此之外,两个突发事件,即王国维和梁启超的先后去世,使得研究院的师生进一步加强了精神联系,借助各种怀念文章,既凝聚了感情,表达了理想,同时也完善了自身形象的塑造。
2005年4月,清华大学历史系举行了纪念清华国学院创立80周年座谈会,我在会上谈及,大家都着力表彰四大导师,这当然没错;可我认为,国学院能有今天的名声,与众弟子的努力分不开。弟子们的贡献,包括日后各自在专业领域取得的巨大成绩,也包括对导师的一往情深,更包括那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为说明这个问题,我提及一本书,即印行于1927年的《清华学校研究院同学录》。这本由吴其昌编辑的小册子,是我所见到的最为精美的“同学录”。除了老师的照片、格言等,最有价值的是每位同学的照片和自述。我的妻子夏晓虹教授专门研究梁启超,对这书很有兴趣,于是和吴其昌女儿吴令华合作,给这本书做注,把这些学生日后的工作业绩,以及他们对国学院生活的描述,对导师和同学的追忆,全都补进来,编成一本别具一格的“学术史”——那就是三联书店2009年刊行的《清华同学与学术薪传》。
在学术史上谈“大学”,一定要把学生的因素考虑进来;学校办得好不好,不仅仅体现在名师的著述,更落实在师生之间的对话与互动,以及学生日后的业绩与贡献。当然必须承认,那些蕴藏在师生情谊背后的理想与情怀,需要某种特殊机缘的激发,方才被公众广泛接纳。最近三十年清华国学院之所以重新焕发耀眼的光辉,与时势迁移,中国学界的目光及兴趣逐渐从政治史转向学术史,有密切关系——这其实是当代中国思想文化潮流变迁的印记。
今天,清华文科声名远扬,但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只是中断近三十年后的重新起步。1978年恢复外语系,那不算什么,任何大学都有公共外语教学;真正有决定性影响的是1985年复建中文系,1993年复建历史系,2000年复建哲学系,至此,清华人文学科才算是全面站稳脚跟。
我的导师王瑶先生晚年多次在私下或公开场合称:“我是清华的,不是北大的。”这个话题我在《八十年代的王瑶先生》(《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中有专门的辨析,这里不赘。1986年王瑶先生撰《念闻一多先生》,“近闻清华大学又在筹建中国文学系”,于是提醒大家注意:“以前的清华文科似乎有一种大家默契的学风,就是要求对古代文化现象作出合理的科学的解释。”1988年王先生又在《我的欣慰和期待》中称:“清华中文系不仅是大学的一个系,而且是一个有鲜明特色的学派。”王先生将“清华学派”的特点概括为以“释古”为旗帜:“他们的治学方法既与墨守乾嘉遗风的京派不同,也和空疏泛论的海派有别,而是形成了自己谨严、开阔的学风的。”原清华中文系主任徐葆耕在收入《王瑶先生纪念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的《瑶华圣土——记王瑶先生与清华大学》中,讲述王先生如何为清华复办中文系出谋划策,值得参阅。日后徐教授出版《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把清华所有著名文科教授都说成是“清华学派”,似乎走过了头;但其在清华校园内不断阐发清华国学院的价值,是有贡献的。我记得很清楚,九十年代初应邀来清华开会,大家纷纷提及清华国学院的传统及贡献(这与中国学界之重新发现王国维与陈寅恪同步),校方是不怎么认可的。
三十多年来,关于清华国学院的表彰,在我记忆中,上世纪九十年代是中文系在追忆,2005年是历史系在纪念,此后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接过大旗来拼命挥舞,声势越来越大。某种意义上,清华大学重新发现并大力阐扬清华国学院的步履,便是新时期清华文科的成长记忆。
如此抚今怀昔,寄托斯文,不仅属于学生,还有学生的学生,以及所谓的私淑弟子——即那些愿意承继并努力追摹的后学。比如,今天清华国学院能有如此声誉,与2009年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的成立有很大关系。作为直属大学的跨学科研究机构,今天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之所以不断讲述“清华国学院”的故事,在我看来乃“公私兼顾”——既有学术理念的坚守,也不无彰显存在、获取经费等现实考量。很可惜,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或称北大文科研究所)虽创办在先,其历史功绩没能得到很好的表彰。其中缘由,北大百年校庆时我曾专门撰文辨析,参见《北大传统:另一种阐释——以蔡元培与研究所国学门的关系为中心》(初刊《文史知识》1998年第5期,收入《老北大的故事》,江苏文艺出版社,1998)。今天的北大研究生院,溯源时偶尔也会提及那段历史,但因自身功能庞杂,实在顾不过来;别的机构又规模太小,承接不上。久而久之,那个同样辉煌的创业故事,也就日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由此可见,对于一个机构或学派来说,筚路蓝缕不容易,但获得后学的仰慕与追随,同样至关重要。
在这个意义上,既祝贺清华国学院百岁不老,青春常在,也祈祷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不辱使命,重铸辉煌!
中央文史馆官员、河南大学近现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陈平原